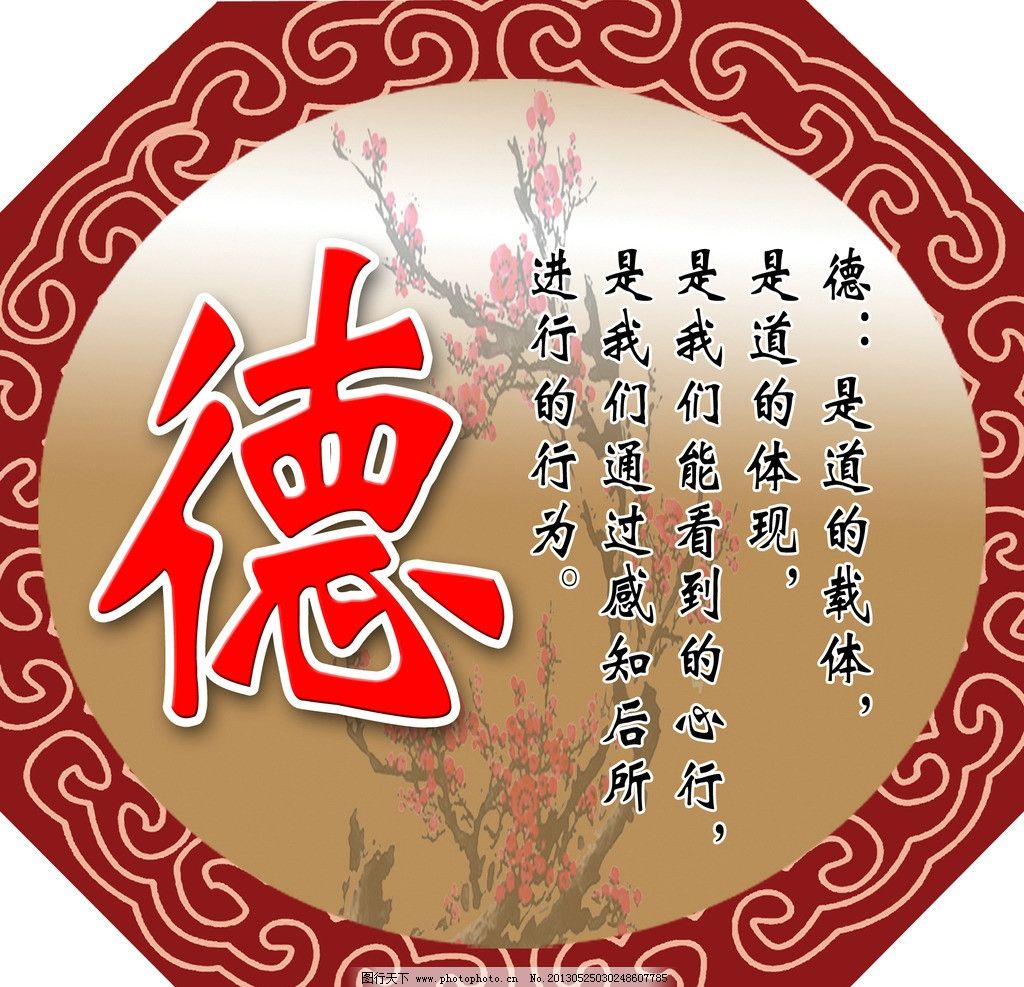
在深厚的儒家傳統里,思想家們的念頭總是在世間,對現實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充滿憂患意識,希望有一種思想能夠徹底地解釋和改造社會。陽明后學同王陽明一樣,遵循著儒家傳統,積極入世,胸懷救世的熱忱,激蕩思想,奔走呼告,期望他們所堅持的理想信念、學術思想以及他們所從事的講學和社會教化活動能夠影響政治,進而實現理想的秩序。
一
自王陽明立學以來,其門人和后學秉持王陽明心學精神,或延伸王陽明的心學思考,或解釋和宣傳王陽明的思想,或將心學精神貫徹到社會生活中去,從不同的角度、層次、領域發揚著王陽明的思想。在政治哲學思想領域,情況同樣如此。在“化治世為治心”這一心學總體政治思路的激發下,陽明后學真誠地相信人的良知可以轉化為救世、治世的根本性力量,在良知的主導下,人們憑借著自己的道德意志、道德情感以及在現實生活中的道德行動,可以實現萬物一體的理想秩序,可以重新回到“三代”社會的理想政治。為此,他們積極從事講學活動、教化活動以及政治活動,以最大的熱情傳播良知之學,改變士風和社會風俗,期望通過啟發廣大民眾特別是鄉村社會的下層民眾,最大程度地發揮自己的良知來從事家庭、家族和鄉村的道德建設,建設一個高舉心體和良知旗幟的理想國。
陽明后學的政治觀念,既反映出他們對于王陽明的信念,也反映出他們對于良知的信念。王陽明以不世之資立不世之功,歷百死千難,所創立的心學、良知學,贏得了后學的膜拜。陽明后學被王陽明傳奇經歷所傾倒,為他的造道精神所折服。他們言必稱王陽明,行必推廣、落實王陽明之學,在中晚明社會掀起一場以王陽明為旗幟的思想運動。王陽明所強調的良知之學,使得陽明后學發現了內在于人心中的道德力量,進而對這種內在的道德力量產生了堅定的信念。當人們孜孜于追求外在天理的時候,王陽明宣稱世界的真相不在對象物那里,而在自己的內心,是人的內心給予了對象物的意義。
困惑于當時士人追逐文辭、知行脫節的社會風氣的陽明后學,豁然覺察到造成這些“假道學”、虛假學風文風、口是心非現象的原因,正是因為人們盲目地追逐外在事理,馳求多端而遺忘了道德行動的源頭恰恰在自己的內心良知,而不是外在的利益、功名。一旦實現了從天理到良知的外內翻轉,陽明后學便堅定地相信只有良知所代表的內在道德意志和情感才能真正地實現現實的道德行動,沒有內在力量的支撐和決定,所有的“道德行動”都不過是一種劇場的假象,是道德的表演,而不是真正發自內心的道德行動。道德表演因為具有可模仿性,故而人們完全可以通過道德表演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社會就在道德表演中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乃至不治。
只有人們是真正地按照自己的道德意志和情感來安排行動,也就是按照良知行事,社會上的道德表演才會逐漸減少,而真正的道德社會才會產生。正是認識到王陽明良知學的苦心孤詣之所在,陽明后學在感性的信仰王陽明的基礎上,又形成了對其良知學說的理性信念。他們把良知當做“元神”“總持”“靈明”“善惡之則”。
二
深受王陽明的影響,在陽明后學心目中,好的政治、合乎道德的政治建立在“萬物一體”的秩序觀上,其具體的、可參照的歷史形態是“三代之治”。“萬物一體”是宋明以來儒家觀看世界的一種視角,自張載、程顥以來,儒家用一種物我同體的視角來進一步詮釋先秦儒家的仁愛之心。換句話來說,什么是仁愛之心以及仁愛之心如何呈現出來?那就是將他人、外物都看作是與自己有著血緣宗法之關系、休戚與共之關聯的存在者。墨子式的將父兄與路人同等對待固然不符合儒家的情懷,但是反過來,如果以父兄之情對待原不與自己相關的路人,那么這種寬廣胸懷則是儒家倡導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陽明提出“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并被后學不斷弘揚。他人不是地獄,而是與自己同呼吸、共命運的存在物,甚至王陽明說我們對禽獸、草木、瓦石所蘊含的不忍之心都是“萬物一體”情懷的體現,更何況那些和我們同類的人。在這種觀看世界方式的主導下,“萬物一體”就變成了一種存在者之間的秩序關系。圣人與我、我與他人、他人與他人之間,都是一體同心,人人比屋可封,一人不安就是己不安,一人困頓就是己困頓,每個人都是命運共同體里的一員。同時,由于每個個體的良知都是相同的,差別僅僅在于不同的人意識到自己良知的程度以及在現實生活踐行良知的能力不一樣,既然良知人人固在,每個人成為圣人的可能性是一樣的,那么人就在本質上具有平等性。“萬物一體”的秩序觀與“人人皆有良知”的倫理觀相結合,便產生了一種具有現代性意義的平等意識。當然,陽明后學的時代完全不可能將這種平等意識在權利義務的層面上表達出來,只是強調在成為圣人的可能性上是平等的。儒家學者所能想象的理想政治,就是上古的“三代之治”。為此,陽明后學不斷重復描述“三代之治”的美好藍圖,并借助“三代之治”批評當時的政治,強調“三代之治”的道德合目的性以及治理上的合理性。
為了實現“萬物一體”的理想秩序以及重新回到“三代之治”,除了在理論上繼續深化王陽明的良知學之外,陽明后學還積極地從事講學和社會教化活動,落實儒者力所能及的政治擔當。基于對陽明心學的信念,他們不遺余力組織講會、開辦書院,四處宣講和推廣良知學,最大限度地鼓動人們信仰良知學并按照良知過一種符合儒家道德的生活。即使是在他們擔任繁重的行政職務時,他們也往往利用手中的行政資源來開展講學運動。而且,他們將“為學”與“為政”看成是一回事,“為學”就是一樁具有政治意義的理論活動,而“為政”也是“為學”的延續和具體落實。“政學一體”的觀念,使得他們認為“為學”一樣是在進行政治建設,是在為治平天下貢獻理智力量,這樣就滿足了他們作為“師儒”的政治使命感;同時也使得他們認為“為政”不是利祿之事,而是儒家之道的具體落實,也是“為學”效果的體現,這樣就從“道”的層面升華了從事政務活動的超越性意義。
陽明后學的政治擔當還體現在廣泛的社會教化活動上,也就是“覺民行道”。陽明后學把目光投向了民間社會。雖居江湖之遠,但他們一樣可以通過切實的鄉村道德建設來落實政治關懷、實現政治理想。他們參與家譜、族譜的編訂,參與鄉規、民約的制定,參與鄉村的勸善運動,參與民間社會的禮教推行,利用多種形式在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將儒家的道德規則、心學的思維方式、禮教的儀節條目變成生活現實,促成民間社會改善道德風尚、形成良好秩序。雖然我們很難描述陽明后學的社會教化運動取得了多大的實際成效,但是他們“覺民行道”的政治建設路徑還是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這就是,重視民眾的自我拯救要比期待救世主的出現顯得更加現實。
三
以信念和教化為主要特質的陽明后學政治哲學是王陽明心學政治哲學的延續,王陽明心學難以走出儒家道德政治的傳統,存在著過度依賴內在意志和情感而忽略制度建設以及偏向于主觀體驗忽視對象意義等缺陷,在陽明后學那里一樣存在。而且,在很多方面,陽明后學放大了王陽明心學政治觀上存在的問題。對于王陽明的迷信,雖可以理解為一種信念,但同時也是一種束縛,他們不斷樹立王陽明的權威的同時,也陷入了王陽明權威的束縛,故而不能突破師說而別開生面。當然,李贄在突破權威束縛的問題上,無論是理論還是行動上都有著較為突出的表現。而對于良知的信念,也凸顯了陽明后學迷信于人的道德力量,忽視了人性中追求自我欲望的因素,因而不能提出約束人的欲望的制度性存在物,來彌補道德約束的不足之處。
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上,陽明后學也依然走不出傳統儒家“三代之治”的觀念,提不出一種新的政治模式和治理藍圖。在講學和社會教化活動中,雖然表現出了儒家知識分子的政治關懷和公共擔當,但是也過分地夸大了儒者的社會作用,把社會的完善、政治的治理完全寄托在某一思想流派成員的教化上,期望以略顯空洞的說教來改變社會風氣,顯然是不具備現實性的。持有這樣的想法,從政治建設的角度來看,只能顯示他們的“天真”和“迂闊”,當然,這樣是儒家學者求道、行道的某種真誠表現。
良好政治的建設既需要共同體成員堅守對于某種價值的信念,也需要啟發共同體成員平等的廣泛參與。陽明后學對于良知的信念,對于道德政治的執迷,對于教化社會的狂熱,值得后人致以遙遠的敬意和同情的理解。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由之而產生的政治文化模式也發生了劇變。
在社會治理中,人們更加相信法治和技術治理;對理想政治的期待,也從“三代之治”走向了更為多元的廣闊的政治模式;而儒家研習者也由于社會分工的擴大化,從傳統士大夫變成以職業、階層所區分的社會成員,他們的政治關懷、社會擔當有了新的表現形式,而不僅僅是“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的“師儒”。因此,在現代政治生活中,我們在學習和利用王陽明以及陽明后學的思想資源的同時,更要為其注入現代性的因素,構建新的文化模式,在自己的存在和活動過程中,為新時代提供更加有意義的智慧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員、上海大學教授 朱承)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2017年12月1日